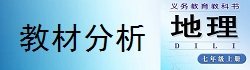罗布泊这个地理名词对上海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因为罗布泊直接牵涉出两个上海人熟知的名字——"彭加木"和"余纯顺"。作为"上海人",他们为上海男人"正名",谁说上海男人都是小男人?彭加木,著名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1980年5月,彭加木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赴新疆罗布泊考察,6月17日,彭加木独自一人到沙漠里找水,不幸失踪,之后一直未找到他的遗体;余纯顺,上海人,1988年7月1日开始孤身徒步全中国的旅行、探险之举。行程达4万多公里,足迹踏遍23个省市自治区。1996年6月,余纯顺在穿越罗布泊沙漠时遇难。这两位,虽然都魂归大漠,却是上海人的骄傲,而同时,罗布泊的名字也"不胫而走",新疆塔里木盆地中,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罗布泊已经成为了又一个"死亡之海"的代名词。

与罗布泊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尽管罗布泊那样遥远,可是有些人,有些事我们不该忘却,罗布泊的消逝带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警示和启迪。
提到罗布泊,有几个人不得不提。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沙皇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斯坦因是其中绕不过去的人物。为纪念中国地理学会成立百年,2009年10月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对百年中国地理大发现作了系统的介绍,其中,斯文•赫定发现楼兰遗址便是由中国地理学会评出的30项100年来最有价值的"中国地理大发现"中的一个。1876年至1877年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新疆探险,他考察了著名的"中亚地中海"罗布泊,然而他亲自抵达的罗布泊,是淡水湖泊,平均水深不足半米,而且位置与中国官方地图(《大清一统舆图》)上那个"罗布泊"不相符,偏南,维度相差有1度。这便是"罗布泊位置之争"的发端。德国地理学家、汉学家冯•李希霍芬认为,在罗布荒原,有一北一南两个湖区,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达的是"南湖",是当地人称为的"喀喇和顺"。而大清地图上标示的罗布泊是"北湖",也是《史记》、《汉书》中所记录的"蒲昌海"。普尔热瓦尔斯基反驳道,"我可是亲眼见过所谓的南湖,但是有谁能证明,果真有那个北湖的存在呢?"于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站了出来,他曾到过新疆,对于一无所知的罗布荒原北部,他准备实地进行考察。1899年,斯文•赫定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新疆,为塔里木东端做地形测量,力图证明中国的历史记载与地图没有错。
与罗布泊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斯文•赫定的考察并没有解决"罗布泊的位置之争",反而引起了更加激烈的"罗布泊游移说"。 (斯文•赫定考察到的其老师李希霍芬预测的"北湖"其实只剩下了干涸的湖床。于是斯文•赫定提出,历史上罗布泊一直存在南北两个湖面,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沉积后抬高了湖底,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邻近处更低的地方流去,又过许多年,抬高的湖底由于风蚀会再次降低,湖水再度回流,这个周期为1600年。"游移说"一度得到广泛支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大规模罗布泊考察活动的展开,而渐渐被推翻。近来的考察普遍认为,罗布泊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有水的,只是水量多少、水质咸淡的分别而已,并没有整体搬迁到过别处。比较能接受的推测是,南北湖的情况由塔里木河等注入罗布泊的水源改道所造成。)尽管如此,斯文•赫定的价值却在于,他在考察罗布泊的同时,意外发现了"楼兰古城",这个20世纪重要的地理大发现缘于著名的"一把铁锹"的故事。
与罗布泊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斯文•赫定在考察罗布荒原期间,向导罗布人奥尔得克把一把铁锹遗忘在荒废的村落里,后来他回去寻找这把铁锹,在风暴中迷路又回归正途,迷路时他闯入了另一个更大的古代遗址,当奥尔得克对斯文•赫定说起这不可思议的经过时,斯文•赫定的眼睛突然就亮了,他知道,奥尔得克忘记带上铁锹不是个过失,而是一种运气。但是由于食物已经不多了,斯文•赫定并不打算冒险,而是按既定路线走出沙漠。1901年,他重整驼队来到罗布泊,终于走进并发现了楼兰。发现楼兰,不是一次考古作业,它的意义在于,作为19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的余波,通过一个古城的重现,带动了对一个地理区域的考察。后来,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在罗布荒原发现了古代楼兰人的墓葬——"太阳墓地";英国人斯坦因发现精绝遗址(斯坦因发现精绝遗址和斯文•赫定进入楼兰古城是新疆探险史进入20世纪的两大标志);日本人释子橘瑞超沿塔里木南缘寻找佛教东传遗迹,在罗布泊获得《李柏文书》的汉代书简;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发现土垠遗址;1934年,年近古稀的斯文•赫定再次来到罗布泊,发现了"有一千口棺木"的小河遗址和著名的"楼兰女尸"。1921年,塔里木河下游改道,河水夺路向东,重新从北面注入罗布泊干湖盆,罗布泊乃一派广阔水域的景象。
与罗布泊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考察罗布泊时也曾发出"塔里木的老虎像伏尔加河的狼群一样多"的感慨。即使是到了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察队在塔里木河汇入罗布泊的湖口地区,看到的还是鸟飞鱼跃的场面。塔里木河下游的胡杨林,红柳等沙生植物形成的绿色走廊蔚未壮观。但现在,罗布泊却又干涸了,这是为什么呢?
罗布泊这一次的消逝绝对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发展史上的悲剧和牺牲品。
斯文•赫定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罗布泊乘过小舟。他坐着船饶有兴趣地在水面上转了儿圈,他站在船头四下远眺,感叹这里的美景。回国后,斯文•赫定在他那部著名的《亚洲腹地探险8年》一书中写道:罗布泊使我惊讶,罗布泊像座仙湖,水面像镜子一样,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乘舟而行,如神仙一般。在船的不远处几只野鸭在湖面上玩耍,鱼鸥及其他小鸟欢娱地歌唱着……
与罗布泊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民国31年(1942),在苏制1/50万地形图上量得罗布泊面积为3006平方公里;1958年,我国分省地图标定面积为2570平方公里;到1962年,航测的1/20万地形图上罗布泊的面积缩减为660平方公里。到1972年,最后干涸部分为450平方公里。被斯文•赫定赞誉过的这片水域居然在20世纪70年代完全消失了,罗布泊从此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30多年时间,这个曾经可能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湖泊竟然完全消逝了。看看《罗布泊,消逝的仙湖》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
"罗布泊的消亡与塔里木河有着直接关系。
塔里木河全长1321公里,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内陆河。据《西域水道记》记载,20世纪20年代前,塔里木河下游河水丰盈,碧波荡漾,岸边胡杨丛生,林木茁壮。问题出在,解放后塔里木河两岸人口激增,水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扩大后的耕地要用水,开采矿藏需要水,水从哪里来?人们拼命向塔里木河要水。几十年间塔里木河流域修筑水库130多座。任意掘堤修引水口138处,建抽水泵站400多处,有的泵站一天就要抽水万多立方米。盲目增加耕地用水、盲目修建水库截水、盲目掘堤引水、盲目建泵站抽水,"四盲"像个巨大的吸水鬼,终于将塔里木河抽干了,使塔里木河的长度由60年代的1321公里急剧萎缩到现在的不足1000公里,320公里的河道干涸,以致沿岸5万多市耕地受到威胁。断了水的罗布泊成了一个死湖、干湖。罗布泊干涸后,周边生态环境马上发生变化,草本植物全部枯死,防沙卫士胡杨林成片死亡,沙漠以每年3米至5米的速度向湖中推进。罗布泊很快与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浑然一体。
罗布泊消失了。"
人们接受教训了吗?当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要"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为什么我的耳朵却感到有些刺痛?如果你关心塔里木河,你会发现,现在不再是下游,而是在塔里木河上游都已经断流了,这条著名的河流是不是会像罗布泊一样从地球上消失呢?你再看看青海湖,青海湖的水面正在不断地下降,有识之士纷纷担忧,千万不能让青海湖变成下一个"罗布泊"啊!再看看四川岷江之上,还有云南正在叫停的那些密密麻麻的水电站、大坝,我们会发现什么?对大自然,我们简直是予取予求啊!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所谓的GDP的需要,我们的步伐从来没有放慢过,我们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从来没有停歇过……
与罗布泊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罗布泊的干涸,只不过是我们在大踏步的追求发展GDP中再简单不过的一种代价。类似的代价触目惊心,不胜枚举。有人说楼兰等西域36国的消亡就是人为导致环境变迁带来的结果,古楼兰人可能没有想过自己的家园会被埋在黄沙之中那么多年。如果这也算是教训的话,我们岂不是在重蹈古人的覆辙吗?
那么,我们能预料什么,我们有能力预料和改变现状吗?我们的未来是罗布泊的昨天还是罗布泊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