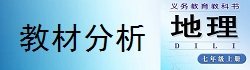从电影《红高粱》看民间文学
与影视开发
摘要:电影《红高粱》是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本文主要探究了其成功的原因,分析电影中所融入的民间故事、民谣和童谣、俚语和谚语等因素,再分析了电影超越民间文学外的深入。最后,指出成功的影视开发必须和谐地运用民间文学的元素,并且以"人性"作为其结合的契机。
关键词: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红高粱》
电影《红高粱》,不仅仅是张艺谋导演生涯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电影的"电影化"历史性革命中的一块里程碑。它的出现,犹如一声霹雳,惊醒了中国人一种新的电影美学观念和审美要求,也惊醒了西方人对中国电影所持的蔑视与迷幻。1988年,该片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录音奖,获得了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获得了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在中国电影尚未摆脱贫瘠的八十年代,《红高粱》囊括了国内外的所有大奖,它的崛起成功地让人嫉妒,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对民间文学的和谐运用,既能融入民间文学,又能跳出民间文学。
一、融入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包括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民间曲艺、民间戏曲等。但是,老的东西终归还是没有新的东西有生命力。在更新换代、优胜劣汰的当今社会,民间文学的传播与发展存在着某些欲说还休的危机。张艺谋以一个第五代导演代表者的身份提出了一个解决的途径: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的融合。在电影《红高粱》中,他便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汲取民间文学的素材以及形式,并将这些元素按功能和旨意重新排列、组装,使电影传递出极具东方神秘感的生命气息和历史回音。电影《红高粱》作为张艺谋电影"民族"特色符号的开端,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对其进行了融合运用:
(一)、民间故事的内容与表达
"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影片在"我"画外音中开始,这种叙述把故事拉远而制造历史的间离效果却又"缝合"了过去与现在、意念与故事,是一种传统民间讲故事的套路式开头。"我"类似的叙述声音间隔地出现12次,贯穿了整部电影,交待了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周围环境、时间转换等几个主要情节转折。有质感的声音加上朴实平淡的口语词汇,模糊了真实与虚构,淡化了时间与空间,从而凸显了故事中的"爷爷"和"奶奶"。故事是否正真地从民间收集整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张艺谋通过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形式叙述营造了民间故事的氛围,迎合了整部片子的表达需要,也满足了观众非常古老而恒久的心理——"听故事"的渴望。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里,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讲述质朴又带有神话色彩、英雄色彩的故事,追忆历史,记录现实,展望未来,通过虚构故事情节达到麻痹自我在现实中生活的困苦情境,通过故事展现自己地区的文化和民风。而在"声色大开"的现代社会,张艺谋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广大人民群众都喜闻乐见的艺术要素,用画面讲述了高粱地里的人和事,展现了十八里坡强悍的民风和凛然的民族正气。
(二)、民歌民谣的热闹与狂欢
民间文学是一种表演性的文学样式,民众是通过声音、表情、动作等来"表演"民间文学。影片中,张艺谋用长镜头、长时间充分地给与了这种民间文学以原姿态的表现方式。
"客未走,席未散,四下寻郎寻不见。
急猴猴,新郎倌,钻进洞房盖头掀。
我的个小乖蛋。
定神看,大麻脸,踏鼻豁嘴翻翻眼。
鸡脖子,五花脸,头上虱子接半豌。
我的个小乖蛋。
丑新娘,我的天,呲牙往我怀里钻。
扭身跑,不敢看,二蛋今晚睡猪圈。"
这是"我奶奶"出嫁的
时候,以"我爷爷"为首的轿夫们吼的《颠轿曲》。漫天黄沙飞舞,喧闹的锣鼓和唢呐,光着膀子的轿夫,一上一下,乎左乎右的脚步。粗犷的声音中带有调笑的祝福。颠轿的折腾是为了营造一种热闹喜庆的氛围,也是将来充满颠簸婚姻的一种于是。轿子里"我奶奶"始终不吭声,还亲不自禁地抽泣了起来,因为她打心底不同意这桩婚事。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
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
从此后,你,搭起那红绣楼呀,
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中我的头呀。
与你喝一壶呀,红红的高粱酒呀,
红红的高粱酒呀,红红的高粱酒呀嘿。"
这是"我奶奶"在回娘家的那天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过之后,"我爷爷"带着激情吼的一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唢呐痛快的呐喊和黄土地男人毫不修饰的粗犷嗓音交相辉映,显示出了野性的激情与大胆。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
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
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
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刹口。
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
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
好酒,好酒,好酒。"
这是酿出高粱酒之后,带有祭祀般神秘豪放的《酒神曲》。它是一种自豪自尊,对劳动本身的礼赞;是一种自由自在,敢爱敢恨的精神。酒是一种属于酒神的东西,它的基本功能在于刺激生命与增殖的欲望。对于酒神的祭拜多多少少也能透出高粱地里的人们旺盛的生命力与毫不掩饰的欲望。此外,酒从远古时代起就与悲剧艺术密切相关。日本鬼子杀害了罗汉大叔之后,黄土地上的汉子再度唱起了《酒神曲》,少了几分夸耀与自傲,多了几分沉重与庄严。同样的民谣变得悲壮,唱出了"我爷爷"他们要为同胞报仇的决心,同时也预示了不可避免的鲜血的悲剧。
"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娘,娘,上西南,溜溜的骏马,足足的盘缠。
娘,娘,上西南,你甜处安身,你苦处化钱。
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这是"我爹"在影片的结尾用高亢童稚的声音为"我奶奶"和三百多个乡亲所吼的一首童谣。童谣本身所表达的内容以及在影片中的运用有着开放式回答的神秘色彩。但是它像是一曲"安魂曲",是对那些热情生命不朽存在的证明。
民歌、民谣用其独特的词、调和表现方式,多层次地展现了中国民间文学所蕴含的狂欢精神。张艺谋将民间文学的情节性与电影的影像性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拉慢了电影的叙事节奏,给观众以充分的时间进行这些"热闹"和"狂欢"背后的理性思索。同时,电影和文学一样,非常注意"陌生化"所带来的效果。距离才产生美感。民歌、童谣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异时"和"异地"性,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三)、俚语、谚语展现的语言张力
电影中的人物语言会自觉地运用很多地方俚语和民间谚语,如"好粱出好酒,好酒出好种","一亩高粱九担半,十个野种,九个混蛋","坏事做尽,好事干绝","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还有很多真性情的骂人的话。虽然这些话之中会有很多性和暴力的影子,但是它们以一种令人想不到的异端的姿态,展现出老百姓最真实的感情倾向,有着真实的温度和质感,拥有受"雅"牵绊的作家文学所无法超越鲜活与生命。这些语言粗俗中又蕴含着生活的哲理,骂出了老百姓心底所淤积的不满与愤懑。张艺谋在电影中加入这些元素,创造了一个感性的、直觉的世界,一个在生命、生存意义的民间社会。
(四)、象征性的电影语言
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的故事,除了有娱乐和艺术的功能之外,还具有艺术和文化的功能。它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不仅仅是因为生命欢娱带给人们的一时刺激,而是在孕育在故事骨髓中的大众审美、民族寓言甚至是意识形态。而在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中,将这些文化和艺术的功能转化为象征性的镜头语言上,主要是色彩和场景之上
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对这部电影的颜色有难以忘却的印象——红色和黄色。红色是女性倔强和激情的一面,而黄色是男性朴实和力量的代表。电影一开篇就以红色为主,"我奶奶"新娘装束是红的,背景也是红色的,一切都隐没在红尘之中。而她坐的轿子以外,主色是黄色,银幕上黄土洼、黄土岗、黄土道贺漫天飞扬的黄色连绵不断。结婚后,新娘子回娘家的那天,"我奶奶"经过高粱地却被"我爷爷"劫走,两种颜色冲破束缚,融合在一起,合二为一。这种色彩的寓意一直延续到了影片的最后,作为电影中"红色"符号的"我奶奶"倒在了红色的血泊之中。这两种最民间的颜色艳丽地让人刺眼,但又是民众内心所隐藏的生命态度。
《红高粱》还以场景表达了高粱地里的人们以对性、对死神力的崇拜,表现了对人的本性中最基质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质力量的崇拜。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然是"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那一段。远镜头俯瞰,"我奶奶"呈红色"大"字状躺在"我爷爷"踩平的高粱地上,"我爷爷"则跪倒在"我奶奶"之前,可谓是一个宗教式性崇拜、生殖崇拜的肃穆仪式。张艺谋在影片中,通过牛被"扒皮"血淋淋的感官刺激,是对死的神力的证明。但是,表达的不是人们对于无法抗拒死亡的悲凉,而是不甘心被屠杀的豪迈。牛的被屠宰与人的被屠宰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影片的结局使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明白:牛是在沉默中被屠宰而成牺牲,人则在爆发的反抗中成就自己的牺牲,并将与屠宰者同归于尽。
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成功地融入民间文学,创造出了一个极具发泄与煽动功能的情感氛围,把感性、娱乐性与理性、严肃性操合在了一起。
二、跳出民间文学
个人认为,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文化的和谐的融合,不能单一地被一种文化所化。单一会让情感和审美趋于一元化,或是热烈地赞美,或是不屑地批判,太过于纯粹而丧失碰撞的火花。所以《红高粱》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他没有单纯地被民间文化所化。但也正是这个因素让张艺谋的电影受人诟病,被指为"伪民俗",被指为没有忠实于现实。我没有切实地考证过是否在那片高粱地上真正出现过类似于"颠轿""祭酒"这样的习俗,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民间性。民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那么民间文学就是再创造,只要每个人都是创作的主体。况且,电影是一种艺术,不是纪录片,"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
而《红高粱》在民间性之外的成功是和时代的思索的碰撞。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刚刚从十年浩劫的阴影中走出,人性复苏、生命意识、生命本能,这些问题成了整个文艺界关注的重点。大家都在用自己的作品反思"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吸取能量继续未来的文艺之路。张艺谋用《红高粱》回答了这个问题:感性地生活。"文革"的十年,过度推崇的是一种压抑情感的生活。理性战胜一切的同时也毁灭了一切。真正的生活是需要冲动的,需要感性的。《红高粱》用宏大的历史母体塑造的是一批叛逆、刚烈而又被欲望支配的存在。矛盾的是,张艺谋坦诚:自已只想拍一部好看的电影,赞颂那片生机勃勃的高粱,以及高粱地里生活的人们。或许,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已的作品会被解读得这么有深度,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觉得时代,至少是影坛缺少这种审美,对于力量感的审美。而这点,恰恰符合了当时的理论探索"人性回归。"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民间文学和影视开发的结合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若能和谐地运用那么这将是一笔双赢的交易。民间文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单单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就提出了2499种类型。这为影视作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另一方面,影视作品的放映,又使影视成为民间文学生成和传播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但并不是所有运用民间文学元素的影视作品都会取得成功,还是以张艺谋的电影为例子。在《红高粱》之后,张艺谋又拍了一系列的"民俗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直到《英雄》的开始,他彻底转战商业片,骂名逐渐高涨。今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使他的骂名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在张艺谋的后期商业片中,也广泛地运用了民间文学的因素,但是并不成功,因为不和谐。在那些电影中,民间文学只是作为一种噱头,作为一种视觉的冲击,作为一种娱乐的手段。所以,民间文学必须和影视开发和谐相处,他们融合的契机应该是"人性",而不是资本或是娱乐。
民间文学可以是伟大的跳板,也可以是陷阱。在长时间舶来西方文化的焦虑和震荡过去之后,我们影视作品已经开始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力量,但这力量与这个时代的期许相比,还远远不够强大。
参考文献:
[1]陈勤建主编 《文艺民俗学论文集》上海文化出版社
[2]朱希祥 李晓华著 《中国文艺民俗审美》上海文化出版社
[3]罗未玮 《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中国期刊网
[4]朱江勇 陈桂成 《〈红高粱〉:一种新型电影美学的开端》中国期刊网
[5]曾耀农 童业富《论第五代导演对历史的阐释》 中国期刊网